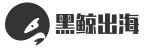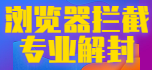т»╣У»ЮТіЋУхёС║║тѕўУі╣№╝џУ«цуЪЦСИЇтцЪ№╝їТЅЇСИЇТЋбтЂџуќ»уІѓуџёС║І
 ТгА
ТгА
ТюгТќЄУйгУЄф№╝џТЎџуѓ╣LatePost№╝ѕID№╝џpostlate№╝Ѕ
ТќЄ№йют«Іуј« у«АУЅ║жЏ» у╝ќУЙЉ№йюж╗ёС┐іТЮ░
РђюVC т»╣У┐ЎСИфСИќуЋїТюђжЄЇУдЂуџёТёЈС╣ЅТў»тѕЏжђаТхЂтіеТђД№╝їУ«ЕСИђС║ЏТюЅТбдТЃ│ТюЅУЃйтіЏ№╝їСйєТў»Т▓АТюЅУЃїТЎ»уџёС║║ТѕљтіЪсђѓРђЮ

тѕўУі╣тЁЦУАїтЂџТіЋУхёжѓБСИђт╣┤№╝їТГБтђ╝СИГтЏйС║њУЂћуйЉУАїСИџт╝ђуФ»сђѓ1999 т╣┤ 1 Тюѕ№╝їжЏитєЏТіЋУхёуџётЇЊУХіуйЉСИіу║┐сђЂ2 ТюѕжЕгтїќУЁЙтЈЉтИЃ OICQсђЂ4 ТюѕжЕгС║ЉтѕЏтіъжў┐жЄїти┤ти┤сђЂ9 ТюѕујІт┐ЌСИют░▒С╗╗Тќ░Тхф CEOсђѓ
21 т╣┤тљј№╝їС║њУЂћуйЉтЁгтЈИС╗јТЌаС║║тюеТёЈуџёУЙ╣у╝ўУДњУЅ▓№╝їТѕљжЋ┐СИ║ТЋ┤СИфСИГтЏйу╗ЈТхјТюђтЁиТ┤╗тіЏуџёжЃетѕєсђѓућџУЄ│№╝їт«ЃС╗гТѕљС║єУ┐ъТјЦСИГтЏйу╗ЈТхјуџёУАђУёЅ№╝їтіажђЪС║єТќ╣Тќ╣жЮбжЮбуџётЈўжЮЕсђѓ
У┐ЎТаиТЃіС║║уџёТѕљжЋ┐тЏаСИ║ТіђТю»У┐ЏТГЦ№╝їтЏаСИ║СИђС╗БС╝ЂСИџт«ХуџётѕЏСИџу▓ЙуЦъ№╝їС╣ЪтЏаСИ║жБјжЎЕУхёТюгуџёТјетіесђѓжБјжЎЕУхёТюгУ«ЕСИђуЙцТюЅТбдТЃ│ТюЅУЃйтіЏ№╝їСйєТ▓АТюЅУЃїТЎ»уџёС║║№╝їТюЅТЏ┤тцџуџёТю║С╝џтѕЏСИџТѕљтіЪсђѓ
тѕўУі╣Тў»С╝┤жџЈУ┐ЎСИђС╗БС╝ЂСИџт«ХТѕљжЋ┐уџёжБјжЎЕТіЋУхёС║║С╣ІСИђсђѓС╗ќ1999т╣┤УхиТГЦС║јждЎТИ»ТЂњжџєжЏєтЏбжЎѕтљ»т«Ќт«ХТЌЈуџёт«ХТЌЈтЪ║жЄЉТЎетЁ┤тѕЏТіЋ№╝ї2008 т╣┤СИјуЪ│т╗║ТўјтѕЏуФІТЎетЁ┤УхёТюг№╝ї2020 т╣┤№╝їТЎетЁ┤УхёТюгТЏ┤тљЇСИ║С║ћТ║љУхёТюгсђѓ
СИЇтљїС║јУ«ИтцџтцДтЪ║жЄЉ№╝їС║ћТ║љТ▓АТюЅуАЁУ░иТЮЦуџётцДтЊЂуЅї№╝їТ▓АТюЅТЌбТѕљуџёТіЋУхёТАєТъХсђѓС╗ЦтЙѕСйјуџёУхиуѓ╣№╝їтЃЈСИђт«ХтѕЏСИџтЁгтЈИСИђТаи№╝їСИђуѓ╣уѓ╣ТЉИу┤б№╝їтйбТѕљСИђтЦЌУЄфти▒уџёТіЋУхёжђ╗УЙЉсђѓС║ћТ║љСИђт║дТў»т░Ју▒│тњїт┐ФТЅІуџёТюђтцДтцќжЃеУѓАСИю№╝їт╣ХТіЋУхёС║єт░Јж╣ЈТ▒йУйдсђЂтЙ«тї╗сђЂтЋєТ▒цуДЉТіђсђЂт░ЈжЕгТЎ║УАїсђЂтю░т╣│у║┐уГЅС╝ўуДђуџёСИГтЏйуДЉТіђтЁгтЈИсђѓ
С║ћТ║љТЅЊТ│ЋуџёТаИт┐ЃТў» РђютЈЇтЁ▒У»є + УХЁжЁЇРђЮсђѓСйєУЄф 2015 т╣┤С╗ЦТЮЦ№╝їжЄЈтїќт«йТЮЙТћ╣тЈўС║єТіЋУхёжђ╗УЙЉ№╝їТ╗┤Т╗┤жЮаУхёТюгуЃДТѕљтИѓтю║уггСИђ№╝їУй»жЊХТѕљуФІтЇЃС║┐уЙјтЁЃуџёУХЁу║ДтцДтЪ║жЄЉсђѓ
тјЪТЮЦУхќС╗ЦТѕљтіЪуџёТЅЊТ│ЋУ«ЕС║ћТ║љтюеТќ░жђ╗УЙЉСИІжћЎУ┐ЄС║єСИђС║ЏтЦйтЁгтЈИ№╝їућџУЄ│жћЎУ┐ЄСИђТЋ┤СИфућхтЋєУхЏжЂЊсђѓРђюТѕЉуќ»уІѓуџёС┐Ат┐ЃтЈЌТЇЪРђЮсђѓ
СИјТГцтљїТЌХ№╝їСИќуЋїт»╣уДЉТіђтЁгтЈИ№╝їтЈітЁХУЃїтљјтіЏжЄЈуџёТђЂт║дС╣Ът╝ђтДІтЈўтїќсђѓ
сђіу║йу║дт«бсђІ11 ТюѕтѕітЈЉсђіжБјжЎЕУхёТюгтдѓСйЋУ«ЕУхёТюгСИ╗С╣ЅтЈўтЙЌуЋИтйбсђІ№╝їС╗Ц WeWork уџёжЌ╣тЅДуЏўтцЇ VC С╗гтдѓСйЋж╝Њті▒У┐Єт║дтєњжЎЕ№╝їтдѓСйЋСИ║С║єтѕЕуЏіТћЙт╝ЃтјЪтѕЎсђЂућџУЄ│ТћЙС╗╗тіБтИЂжЕ▒жђљУЅ»тИЂсђѓ
т»╣С║јУхёТюгт║ћУ»ЦТћ»ТїЂС╗ђС╣ѕТаиуџётЁгтЈИтњїУАїСИ║№╝їтѕЏжђаТђјТаиуџёуцЙС╝џС╗итђ╝№╝їтѕўУі╣ТюЅУЄфти▒уџёуюІТ│Ћсђѓ
С╗ЦСИІТў»сђіТЎџуѓ╣ LatePostсђІСИјтѕўУі╣уџёт»╣У»Ю№╝џ
┬аРђюуљєУДБСИђСИфтЪ║жЄЉуюЪТГБуџёТіЋУхёТѕљу╗ЕтЁХт«ъТў»СйауџёТЌХжЌ┤У┤ежЄЈРђЮ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ТѕЉС╗гтЁѕТЮЦтЏъжАЙСИђСИІУ┐ЄтЙђсђѓСйауџёуггСИђТюЪтњїуггС║їТюЪтЪ║жЄЉтѕєтѕФтѕЏжђаС║є 50 тђЇтњї 30 тђЇуџёТіЋУхётЏъТіЦујЄсђѓТћЙтюеС╗ітцЕТЮЦуюІ№╝їУ┐ЎТў»тљдТў»СИђСИфтЦЄУ┐╣№╝Ъ
тѕўУі╣№╝џСИђт«ХтЪ║жЄЉуџётЏъТіЦтдѓТъютюе 3 тѕ░ 5 тђЇ№╝їт░▒ти▓у╗ЈСИЇжћЎ№╝їтдѓТъюУЃйУХЁУ┐ЄтЇЂтђЇ№╝їТў»УАїСИџжЄїжАХт░ќсђѓУђїУ┐ъу╗ГСИцТюЪТюЅтЄатЇЂтђЇтЏъТіЦтЪ║жЄЉ№╝їтЁеСИќуЋїС╣ЪСИЇтцџУДЂ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 50 тђЇтњї 30 тђЇС╣ІжЌ┤№╝їти«УиЮТЮЦУЄфС╗ђС╣ѕ№╝Ъ┬а
┬атѕўУі╣№╝џтЏъТіЦтђЇТЋ░у╗ЈтИИТ│бтіе№╝їуггСИђТюЪтЪ║жЄЉУЃйУДЂт║дТюђжФў№╝їС║їТюЪтЪ║жЄЉС╗ітцЕТў» 30 тђЇ№╝їтЈ»УЃйУ┐ўТў»УбФСйјС╝░С║є№╝їтЙѕтцџжА╣уЏ«У┐ўтюеУиЉуџёУи»СИісђѓ
У┐Єтј╗тЁеСИќуЋїТюђжФў ROI№╝ѕТіЋУхётЏъТіЦујЄ№╝Ѕуџёу╗ЈТхјСйЊТў»СИГтЏй№╝їСИГтЏйТюђжФў ROI уџёУАїСИџТў» TMTсђѓСИђСИфтЪ║жЄЉтљѕС╝ЎС║║ТЏЙжЌ«ТѕЉ№╝їРђюУ┐Єтј╗тЇЂтЄат╣┤жЄї№╝їТюЅтЊфСИђСИфТѕЉС╗гуЪЦжЂЊуџётЪ║жЄЉСИЇТїБжњ▒№╝ЪРђЮ
ТЅђС╗ЦтЏъТіЦтЦйСИЇТў»ТѕЉС╗гуџёУЃйтіЏ№╝їТѕЉС╗гтЈфТў»ТЂ░тЦйтюеУ┐ЎТаиСИђСИфтЉеТюЪжЄїтЂџт»╣С║єсђѓтЈЇУ┐ЄТЮЦУ┐ЎС╣ѕТЃ│№╝їСйаС╣░У┐ЄТѕ┐тГљтљЌ№╝Ъ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С╣░У┐Єсђѓ
тѕўУі╣№╝џТЅђС╗ЦСйаТѕљтіЪтЂџС║єСИђТгАТіЋУхёсђѓУ┐Ўт░▒Тў»ТѕЉС╗гУ┐ЎСИђС╗Буџё lucky№╝їСйатюежѓБСИфТЌХТю║С╣░С║єТѕ┐тГљ№╝їТѕЉтюежѓБСИфТЌХТю║тЂџС║єТіЋУхё№╝їТ▓АС╗ђС╣ѕТюгУ┤еСИЇтљї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СйєСИцСйЇТЋ░уџётЏъТіЦ№╝їУѓ»т«џТў»тЂџт»╣С║єТЏ┤тцџС║Ісђѓ
тѕўУі╣№╝џтЏъТіЦтЈфТў»у╗ЊТъюсђѓуљєУДБСИђСИфтЪ║жЄЉуюЪТГБуџёТіЋУхёТѕљу╗ЕТў»СйауџёТЌХжЌ┤У┤ежЄЈ№╝їСйауџёТЌХжЌ┤Тў»СИЇТў»Уі▒тюеТюђтђ╝тЙЌУі▒ТЌХжЌ┤уџёС║║У║ФСИі№╝їС╗ЦтЈіСйаТ»ЈтцЕУиЪжѓБС║ЏС║║У«еУ«║уџёС║ІТЃЁТў»тљдтюеТюфТЮЦтЇЂт╣┤С╝џтИдТЮЦуюЪТГБтиетцДуџёС╗итђ╝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тЈ»тљдтѕєС║ФСИђСИфСйатЇЂт╣┤тЅЇтЂџуџё№╝їтй▒тЊЇтљјТЮЦтЇЂт╣┤т╣ХтИдТЮЦУХЁтцДтЏъТіЦуџёТіЅТІЕсђѓ
тѕўУі╣№╝џТѕЉ 1999 т╣┤тіатЁЦТЎетЁ┤тѕЏТіЋ№╝їжѓБТў»ТЂњжџєжЏєтЏбжЎѕТ░Јт«ХТЌЈуџёт«ХТЌЈтЪ║жЄЉсђѓ2005 т╣┤уггСИђТЅ╣уЙјтЏй VC У┐ЏСИГтЏй№╝їУ┐Ўт╝ЋтЈЉС║єТѕЉС╗гтє│т«џтюе 2007 т╣┤Тііт«ХТЌЈтЪ║жЄЉтЈўТѕљуюЪТГБ LPРђћGP уџёу╗ЊТъёсђѓтйЊТЌХтЙѕтцџуЙјтЏйтЪ║жЄЉТѕќТўјТѕќТџЌТЃ│ТііТѕЉС╗гтЏбжўЪТћХС║є№╝їСйєТѕЉТЃ│СИђуѓ╣СИђуѓ╣ bulid СИђСИфУЄфти▒уџётЪ║жЄЉсђѓ
2008 т╣┤ТўЦУіѓ№╝їТѕЉтюетцќжЮбтІЪУхё№╝їУи»СИіт░▒жЂЄСИіС║єжЄЉУъЇтЇ▒Тю║№╝їжЮътИИтЏ░жџЙсђѓТюђтљјтіаСИіжЎѕТ░Јт«ХТЌЈТјЈуџёСИђСИфС║┐№╝їТѕЉС╗гТЅЇтІЪтѕ░С║є 1.5 С║┐уЙјтЁЃ№╝їУ┐ЎТў»уЅ╣тѕФтцДуџёТћ»ТїЂсђѓ┬а
ТѕЉУ«░тЙЌтЙѕТИЁТЦџ№╝їтйЊТЌХтњїСИђСйЇ LP С║цТхЂ№╝їС╗ќжЌ«ТѕЉСИ║С╗ђС╣ѕУдЂтЂџУ┐ЎСИфтЪ║жЄЉ№╝ЪТѕЉУ»┤тЙѕу«ђтЇЋ№╝їТѕЉт░▒ТЃ│УЄфти▒тЂџСИђСИфСИГтЏйТюђС╝ўуДђуџёТЌЕТюЪТіЋУхётЪ║жЄЉсђѓ
LP тљгт«їУ»┤С╗ќтЙѕтќюТгбТѕЉУ┐ЎСИфТЋЁС║І№╝їтљјТЮЦС╗ќТѕљСИ║С║єС║ћТ║љуггСИђСИф LP№╝їжѓБТюЪтЪ║жЄЉС╣ЪТў»ТѕЉС╗гТюЅтЈ▓С╗ЦТЮЦтЏъТіЦТюђтЦйуџётЪ║жЄЉ№╝їТѕЉС╗гу╗ЎС║єС╗ќтЄатЇЂтђЇуџётЏъТіЦсђѓ
РђюУ«ЕС╝ЂСИџт«ХТѕљСИ║ТѕЉС╗гуЪЦУ»єуџёСИђжЃетѕєРђЮ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СИ║С╗ђС╣ѕТћ╣тљЇ№╝Ъ
тѕўУі╣№╝џтйЊТЌХтЄ║ТЮЦтѕЏСИџ№╝їтІЪУхёУЅ░жџЙ№╝їт«ХТЌЈтЪ║жЄЉТЎетЁ┤тѕЏТіЋу╗Ўжњ▒сђЂу╗ЎтЊЂуЅїтљЇТћ»ТїЂсђѓТюђУ┐ЉСИцт╣┤тЏаСИ║т░Ју▒│сђЂт┐ФТЅІуГЅТўјТўЪжА╣уЏ«№╝їтЙѕтцџтЏйтєЁтцќтфњСйЊтњїтѕЏСИџУђЁТЅЙУ┐ЄТЮЦ№╝їС╗ќС╗гтѕєСИЇТИЁТЎетЁ┤тѕЏТіЋтњїТЎетЁ┤УхёТюг №╝їтЁЇСИЇС║єС╝џТЅЊТЅ░тѕ░т«ХТЌЈтЪ║жЄЉуџёС╝ЎС╝┤С╗гсђѓТЅђС╗ЦС╣ЪуА«т«ъУ»ЦТІЦТюЅУЄфти▒уџётљЇтГЌС║є№╝їС╗іт╣┤ТГБт╝Јтљ»уће РђюС║ћТ║љУхёТюгРђЮ№╝їУІ▒ТќЄтљЇтЈФ Рђю5Y CapitalРђЮ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СйаТюђТЌЕтЄаугћС║њУЂћуйЉТіЋУхётѕєтѕФТў» UCсђЂYY тњїУ┐ЁжЏи№╝їТў»тдѓСйЋтЈЉуј░т╣ХТіЋУхёС║єС╗ќС╗г№╝Ъ
тѕўУі╣№╝џТѕЉтйЊТЌХуюІТИИТѕЈ№╝їСИђт╣┤тЄаС╣јТ»ЈТЎџжЃйТ│АтюеуйЉтљД№╝їтњїуйЉтљДжЄїуџёС║║СИђУхиТии№╝їТЃ│уюІС╗ќС╗гтюет╣▓тўЏсђѓтйЊТЌХУ«цУ»єС║єСИђСИфТИИТѕЈтЁгС╝џуџёС╝џжЋ┐№╝їУДЅтЙЌтЙѕТюЅТёЈТђЮсђѓтљјТЮЦжЏитєЏу╗ЎТѕЉС╗Іу╗ЇС║єТЮјтГдтЄї№╝їТЮјтГдтЄїУ»┤С╗ќТљът«џС║є 10 СИЄСИфтЁгС╝џ№╝їС╗ќУ»┤С╗ќС║║тюет╣┐тиъ№╝їТѕЉт░▒тј╗С║єсђѓ
2006сђЂ2007 т╣┤ТѕЉТІјуЮђСИђСИфтїЁ№╝їт╣┐тиъТи▒тю│ТіўУ┐ћУиЉ№╝їтйЊТЌХТ▓АТюЅтїЌС║гСИіТхиуџёТіЋУхёС║║уюІжѓБУЙ╣№╝їС║јТў»ТѕЉСИђСИфС║║ТіЋС║єт╣┐СИютЦйтЄаСИфС║њУЂћуйЉтЁгтЈИ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уј░тюеУ┐ўТюЅТІјуЮђтїЁтѕ░тцёуюІжА╣уЏ«уџёТЌХтђЎтљЌ№╝Ъ
тѕўУі╣№╝џТѕЉтцЕтцЕСИЇжЃйтюеУ┐Ўтё┐тљЌ№╝Ъ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СйатюеС║ћТўЪу║ДжЁњт║ЌуџёУАїТћ┐жЁњт╗іжЄїсђѓ
тѕўУі╣№╝џтйбт╝ЈСИЇжЄЇУдЂ№╝їжЄЇУдЂуџёТў»ТѕЉтјЪТЮЦТў»СИђСИфС║║№╝їС╗ітцЕТѕЉтюетИдтіеТЋ┤СИфу╗ёу╗Єт╗║уФІТЏ┤т╝║тцДуџёУ«цуЪЦ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СйаС╗гТіЋУхёуџёуЅ╣уѓ╣Тў»т░ЉТіЋу▓ЙСйю№╝їСИ║С╗ђС╣ѕС╝џтйбТѕљУ┐ЎТаиуџёТіЋУхёжБјТа╝№╝Ъ
тѕўУі╣№╝џТюЅтјєтЈ▓УЃїТЎ»№╝їжѓБТЌХтђЎућет«ХТЌЈуџёУхёжЄЉТіЋУхё№╝їТ▓АТюЅУ┐йТ▒ѓТЅђУ░ЊтЙѕТ┐ђУ┐ЏуџёУдєуЏќ№╝ЏуггС║ї№╝їТѕЉС╗гС║║С╣ЪтЙѕт░Љсђѓ
тдѓТъюу│╗у╗ЪТђДуљєУДБС║ћТ║љуџёти«т╝ѓтїќТЅЊТ│Ћ№╝їТаИт┐ЃтюеС║јТѕЉС╗гУиЪтИѓтю║СИітЁХС╗ќтЪ║жЄЉуЏИТ»ћ№╝їтЁиТюЅСИђуДЇжЮътЁ▒У»є№╝їтйЊтцДт«ХТ▓АТёЈУ»єтѕ░СИђС║ЏСИюУЦ┐уџётЦй№╝їТѕЉС╗гУЃйтЈЉуј░т«ЃуџётЦйсђѓУ┐Ўт░▒т»╣СйауџёУ«цуЪЦТЈљтЄ║С║єтЙѕжФўуџёУдЂТ▒ѓ№╝їждќтЁѕУ«цуЪЦУдЂтцЪТи▒№╝їуггС║їУдЂТюЅтЅЇуъ╗ТђД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т»╣С║јтЂџСИђС║ЏтцДт«ХжЃйУДЅтЙЌСИЇт»╣уџёС║І№╝їСйаС╝╝С╣јТ▓АС╗ђС╣ѕТђЮТЃ│тїЁУб▒сђѓ
тѕўУі╣№╝џТѕЉТюђтцДуџёС╝ўуѓ╣Тў»Т▓АТюЅТАєТъХсђѓтЙѕтцџтљїУАїТюЅтЊЂуЅї№╝їТюЅуАЁУ░иТЋ┤СИфУ«цуЪЦСИіуџётЦЌтѕЕС╝ўті┐№╝їТѕќУђЁС╗јС║їу║ДтИѓтю║тИдуЮђтцДУхёжЄЉУиеУ┐ЄТЮЦсђѓС║ћТ║љТў»СИђСИфу║»тюЪж│ќуџётЏбжўЪ№╝їТѕЉС╗гУхиуѓ╣Сйј№╝їт░▒тЃЈСИђСИфтѕЏСИџтЁгтЈИ№╝їтЈфУЃйТЁбТЁбТЉИу┤бсђѓ
тЈ»УЃйтЏаСИ║У┐ЎТ«ху╗Јтјє№╝їТѕЉт»╣жѓБС║ЏжЮътЁ▒У»єсђЂСИЇСИ╗ТхЂуџётѕЏСИџУђЁ№╝їТ»ЈТгАжЃйУЃйтюежЮътИИуЪГТЌХжЌ┤тєЁС║ДућЪтЙѕт╝║уџёсђЂТё┐ТёЈт░ЮУ»Ћуџётє▓тіесђѓУђїТѕЉС╗гС╣ІТЅђС╗ЦТіЋУхёТѕљу╗ЕтЦй№╝їТў»тЏаСИ║ТѕЉС╗гуЅ╣тѕФУЃйуљєУДБтЈЇтЁ▒У»єтњїтЈЇтИИУДёТў»ТюђжЄЇУдЂуџё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жЏитєЏтѕЏуФІт░Ју▒│ТЌХТў»СИђСйЇТўјТўЪтѕЏСИџУђЁ№╝їСИЇС╗ЁСИ╗ТхЂ№╝їУ┐ўТў»тЙѕтцџуеІт║ЈтЉўуџётЂХтЃЈсђѓ
тѕўУі╣№╝џТѕЉС╗г 2010 т╣┤ТіЋт░Ју▒│уџёТЌХтђЎ№╝їСйаУДЅтЙЌТ▓АС║ЅУ««тљЌ№╝Ъ
т░Ју▒│тйЊТЌХТЈљтЄ║С║њУЂћуйЉуАгС╗ХТїЅТѕљТюгт«џС╗и№╝їТ▓АТюЅС║║уљєУДБсђѓТѕЉС╗гУ┐ъу╗ГСИЅУй«ТіЋУхё№╝їт░Ју▒│ 2000 СИЄуЙјтЁЃС╝░тђ╝ТЌХТіЋС║є 500 СИЄ№╝ї2 С║┐С╝░тђ╝ТЌХТіЋС║є 1000 СИЄ№╝ї10 С║┐уЙјтЁЃТЌХ№╝їтЁгтЈИУ┐ўТ▓АУхџжњ▒№╝їТѕЉС╗гтє│т«џжбєТіЋсђѓ
т░Ју▒│Тў»СИђТюЪуџёжА╣уЏ«№╝їТѕЉС╗гСИ║ТГцт╝ђС║єС║їТюЪ LP уџёС╝џУ««№╝їУ»┤ТюЇ LP ућеС║їТюЪуџёжњ▒ТЮЦжбєТіЋ№╝їТІ┐Тќ░тЪ║жЄЉуџёжњ▒ТЮЦтЁ╗УђЂтЪ║жЄЉуџёжА╣уЏ«№╝їУ┐ЎТў»жЮътИИт┐їУ«│уџёсђѓСйєТѕЉС╗гУ┐ўТў»тЂџтѕ░С║єсђѓ
2015 т╣┤№╝їСйЎтЄ»С╗јуЎЙт║дтЄ║ТЮЦ№╝їСИђтцЕУі»уЅЄТ▓АтЂџУ┐Є№╝їС╗ќУ»┤УдЂтЂџУі»уЅЄсђѓтЏаСИ║С╗ќУ»┤СИІСИђС╗БтЂџ AI Уі»уЅЄуџёт║ћУ»ЦТў»ТЄѓу«ЌТ│ЋтњїУй»С╗ХуџёС║║сђѓтйЊТЌХтЁгтЈИжЃйТ▓АТѕљуФІ№╝їТѕЉт░▒ТіЋС║єС╗ќсђѓТіЋС╝ау╗ЪУі»уЅЄуџёС║║Тў»СИЇС╝џТіЋтю░т╣│у║┐уџё№╝їС╗ќС╗гтЈфС╝џТіЋТюЅ 20 т╣┤Уі»уЅЄу╗ЈжфїуџёС║║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ТюЅС║║У»┤СйаС╗гТў»ућеТіЋС║їу║ДуџёТќ╣т╝ЈТіЋСИђу║ДсђѓТ»ћтдѓуюІСИЇТЄѓСИЇТіЋ№╝їТїЂу╗ГтіаТ│е№╝їУ┐ЎжЃйТў»тЁИтъІти┤УЈ▓уЅ╣т╝ЈуџёТіЋУхёТќ╣Т│Ћсђѓ
┬атѕўУі╣№╝џтцДжЂЊУЄ│у«ђсђѓТЅђТюЅТюђжЄЇУдЂуџётјЪтѕЎтњїТќ╣Т│ЋУ«║жЃйтЈ»С╗ЦућетюеСИЇтљїУАїСИџ№╝їС╗јТЮЦТ▓АТюЅС╗ђС╣ѕС║їу║ДтИѓтю║уџёТќ╣Т│ЋУ«║тњїСИђу║ДтИѓтю║уџёТќ╣Т│ЋУ«║№╝ЏтЁХТгА№╝їу╗ЈтЁИуџёС╗итђ╝ТіЋУхёС║║т»╣уј░жЄЉТхЂуЅ╣тѕФтЮџТїЂ№╝їС╗ќУ«цСИ║тЈфТюЅуј░жЄЉТхЂТЅЇТюЅС╗итђ╝сђѓ
СйєТѕЉУЃйтцЪтюеТ▓АТюЅуј░жЄЉТхЂуџёТЌХтђЎуюІтѕ░т«ЃТюфТЮЦУЃйС║ДућЪуј░жЄЉТхЂуџёУЃйтіЏ№╝їУ┐ЎС╣ЪтЈФС╗итђ╝ТіЋУхё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тдѓСйЋТЅЕт▒Ћтњїт╝║тїќУЄфти▒уџёУ«цуЪЦ№╝Ъ
тѕўУі╣№╝џСИђСИфТў»т»╣С║ІТЃЁсђЂСИђСИфТў»т»╣С║║уџёуљєУДБсђѓ
ТѕЉС╗гуџёТаИт┐ЃуГќуЋЦТў»у▓ЙжђЅ№╝їС╗ЦтЈітюеСИђС║ЏуЅ╣тѕФтЦйуџётЁгтЈИжЄїТЋбС║јУХЁжЁЇсђѓу▓ЙжђЅтњїУХЁжЁЇУЃїтљјСИцуѓ╣№╝їСИђТў»ТѕЉС╗гУиЪжџЈТюђС╝ўуДђуџётѕЏСИџУђЁ№╝їтњїС╗ќС╗гСИђУхиТѕљжЋ┐№╝ЏС║їТў»ТѕЉС╗гтЁ│Т│еС╝ўуДђтѕЏСИџУђЁУЃїтљјуџёуДЉТіђтЈўжЄЈсђѓ
СИ║С╗ђС╣ѕТѕЉС╗гТюђУ┐ЉтЁ│Т│етЇіт»╝СйЊтњїућЪуЅЕтї╗УЇ»№╝ЪтЏаСИ║тЪ║тЏаТхІт║ЈТіђТю»уџёТѕљуєЪУ«ЕтцДжЄЈуЏЉТхІТЋ░ТЇ«С║ДућЪ№╝їУђїТЋ░ТЇ«жюђУдЂу«ЌТ│ЋтњїУй»С╗ХТЮЦУДБтє│сђѓУ┐ЎС║ЏТќ░уџётиЦтЁитЙђтЙђСИЇС╝џУбФС╝ау╗ЪтѕХУЇ»УАїСИџуљєУДБ№╝їУ┐Ўт░▒Тў»ТѕЉС╗гуџёТю║С╝џ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VC т║ћУ»ЦтюеУАїСИџуџётЊфСИфжўХТ«хУ┐ЏтЁЦ№╝ЪућЪуЅЕтї╗УЇ»тњїтЇіт»╝СйЊжЃйТў»тюеС║ћТ║љС║ћТюЪтЪ║жЄЉтљјТЅЇТюЅуџёТќ╣тљЉ№╝їСйєтЈ»УЃйу║бТЮЅтЇЂт╣┤тЅЇт░▒ТюЅС║єсђѓ
тѕўУі╣№╝џждќтЁѕТў»жўЁУ»╗ТіђТю»уџёТѕљуєЪ№╝їтЁХТгАТў»жўЁУ»╗тЋєСИџуџётЈўтїќсђѓжђџтИИТіђТю»ТѕљуєЪСИЇуГЅС║јтЋєСИџТю║С╝џ№╝їТѕЉС╗гтЈФ РђюжбєтЁѕтИѓтю║ 0.5 ТГЦРђЮсђѓСйєуюЪуџётіеТЅІС╣ЪУ«ИУдЂуГЅСИђуГЅ№╝їУ┐ЄТЌЕСИЇСИђт«џТюЅТю║С╝џсђѓуГЅтѕ░тИѓтю║т«їтЁеУхиТЮЦСйат░▒ТЮЦСИЇтЈіС║є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СйєтЇіт»╝СйЊТіЋУхёС╗ітцЕти▓у╗ЈжЮътИИуЂФуЃГС║єсђѓ
тѕўУі╣№╝џТѕЉС╗гУйгтљЉтЇіт»╝СйЊТў»тЏаСИ║уюІтѕ░С║єу╗ѕуФ»уџётЈўтїќсђѓУ┐Єтј╗тЇіт»╝СйЊУАїСИџТў»тЂџС╗БтиЦ№╝їТЅђТюЅуаћтЈЉтњїС║ДтЊЂт«џС╣ЅуџёТ║љтц┤жЃйСИЇтюеСИГтЏй№╝їтЏаСИ║у╗ѕуФ»СИЇтюеСИГтЏйсђѓУђїС╗ітцЕСИГтЏйуџёу╗ѕуФ»тюет┤ЏУхи№╝їТЎ║УЃйТЅІТю║тњїућхтіеУйдуџёжбєт»╝тЊЂуЅїжЃйС║ЅуЮђУдЂт«џС╣ЅСИІСИђС╗БС║ДтЊЂуџёТќ░тіЪУЃйсђѓ
ТѕЉС╗гТіЋС║єт░Ју▒│сђЂт░Јж╣Ј№╝їт░Ју▒│Тўјт╣┤уџёТЅІТю║Тќ╣тљЉТѕќУђЁт░Јж╣ЈСИІСИђС╗БуџёТ▒йУйдС╗ђС╣ѕТаи№╝їтЈфУдЂСИђт«џС╣ЅСИІТЮЦ№╝їС╝џтЈЉућЪУ┐ъжћЂтЈЇт║ћ№╝їТѕљтЇЃСИіСИЄСИфжЏХжЃеС╗ХтјѓтЋєтЁ▒тљїТііС║ДтЊЂти«т╝ѓтїќ№╝їуДЉТіђуаћтЈЉуџёжБъУй«ТЋѕт║ћтюеСИГтЏйт░▒тЄ║уј░С║єсђѓ
СИ║С╗ђС╣ѕТѕЉС╗гС╗ітцЕТЅЇтЂџУ┐ЎС╗ХС║Ітё┐№╝їТў»тЏаСИ║ТѕЉтюеУ┐ЎСИфС║ДСИџжЄї№╝їТѕЉтюеУЉБС║ІС╝џСИі№╝їТѕЉуюІтѕ░С║єТю║С╝џ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ТЅђС╗ЦСйаУЃйуюІтѕ░СИђС║ЏТю║С╝џ№╝їТў»тЏаСИ║СйаУиЪСИђу║┐уџёС╝ЂСИџт«ХТюЅТЏ┤Ти▒тЁЦуџёТ▓Ъжђџ№╝Ъ
тѕўУі╣№╝џТў»уџёсђѓтЙѕтцџС║║У»┤ТѕЉС╗гт»╣С║ДСИџсђЂт»╣ТіђТю»тЙѕТЄѓ№╝їСИЇтдѓУ»┤ТѕЉС╗гт»╣С║║ТЏ┤ТЄѓсђѓС╝ЂСИџт«ХС╝џТѕљСИ║ТѕЉС╗гуЪЦУ»єуџёСИђжЃетѕє№╝їтЈѓСИјТѕЉС╗гуџёУ«еУ«║сђѓ
тйЊСйаУі▒С║єтЙѕтцџу▓ЙтіЏтюежўЁУ»╗УХІті┐уџётљїТЌХ№╝їС╝џтЈЉуј░ТюЅтЄаСИфтГцуІгуџётѕЏСИџУђЁС╣ЪтюежѓБ№╝їС╗ќС╗гуџё Vision тњїТѕЉС╗гт»╣УХІті┐уџё Vision Тў»тЁ▒Тї»уџё№╝їТЅђС╗ЦТѕЉС╗гтЈЉуј░т╣ХУ»єтѕФС║єС╗ќС╗гсђѓ
┬аРђюУдєуЏќтъІТЅЊТ│ЋуџётЏъТіЦТЏ┤ТјЦУ┐Љ╬▓сђѓтЈфТюЅСйажђЅтЙЌтЄє№╝їСйаТЅЇУЃйтѕЏжђаТЏ┤тЦйуџё╬▒тЏъТіЦсђѓРђЮ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т░Ју▒│СИітИѓуџёТЌХтђЎ№╝їтюеТЃ│С╗ђС╣ѕ№╝Ъ┬а
тѕўУі╣№╝џТѕЉтюеТЃ│тЁгтЈИТђјС╣ѕУЃйтцЪтЈўТѕљСИђтЇЃС║┐сђѓ┬а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С╝џТІЁт┐ЃтєЇС╣ЪТіЋСИЇтЄ║Т»ћт░Ју▒│тЏъТіЦТЏ┤тЦйуџёжА╣уЏ«тљЌ№╝Ъ┬а
┬атѕўУі╣№╝џС╗јтЂџТіЋУхёТЮЦУ«▓№╝їТюђТѕљтіЪуџёжЃйТў»СИІСИђТГЦ№╝їтљдтѕЎСйаС╝џу╝║С╣ЈТЅђТюЅТіЋУхёуџёуЃГТЃЁ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С║ћТ║љТў»сђїт░ЉТіЋу▓ЙтЂџсђЇуџёС╗БУАе№╝їжџЈуЮђтЙѕтцџтЪ║жЄЉУхёС║ДУДёТеАТъЂжђЪТЅЕтцД№╝їУ┐Єтј╗тЄат╣┤С║ћТ║љуџёТЅЊТ│ЋТў»тљджЂЄтѕ░С║єтЏ░жџЙ№╝Ъ
тѕўУі╣№╝џ2013 тѕ░ 2016 т╣┤Тў»ТЋ┤СИфТіЋУхёУАїСИџтЁгУ«цжЮътИИтЏ░жџЙуџёт╣┤С╗й№╝їТЅђТюЅ VC/PE тЏъТіЦжЃйтюеу│╗у╗ЪТђДСИІжЎЇсђѓжѓБС╣ЪТў»ТѕЉС╗гУ┐ЎтЦЌТіЋУхёТќ╣Т│ЋТюђжђєжБјуџёТЌХтђЎ№╝їС╗ЦУЄ│С║јТѕЉСИђт║дтюеТЃ│Тў»СИЇТў» VC уџёТИИТѕЈУДётѕЎтЈўтїќС║єсђѓ
ТѕЉС╗гтјЪТЮЦУ┐йТ▒ѓтюеТЌЕТюЪтЄ╗СИГжА╣уЏ«№╝їжњ▒СИЇТў»ТхижЄЈТЌХ№╝їУ┐ЎуДЇТќ╣Т│ЋТў»ТюђТюЅТЋѕуџёсђѓСйє 2013 т╣┤тљјтЄ║уј░С║єСИђСИфтцДтЈўтїќРђћРђћжЄЈтїќт«йТЮЙС╣ІтљјУхёТюгСИЇтєЇуеђу╝║№╝їТхижЄЈуџёжњ▒тє▓У┐ЏС║єУѓАтИѓтњїуДЉТіђтЁгтЈИсђѓ
ТѕЉС╗г 2012 т╣┤ТіЋУхёТўЊтѕ░№╝їтйЊТЌХТ╗┤Т╗┤У┐ўТ▓АТюЅТѕљуФІсђѓТѕЉС╗гС╗јТ▓АТЃ│тѕ░СИђт«ХтЁгтЈИтЈ»С╗ЦУъЇ 150-200 С║┐уЙјтЁЃ№╝їУхёжЄЉУДёТеАУ┐ЁжђЪТЉДТ»ЂС║є first mover№╝ѕТеАт╝ЈждќтѕЏУђЁ№╝ЅтЁѕтЈЉС╝ўті┐№╝їтє▓тъ«С║єСйаСйюСИ║СИђСИфу╗ЈтЁИ VC уџёУ«цуЪЦС╝ўті┐сђѓтдѓТъюТ▓АТюЅТ╗┤Т╗┤т┐ФуџёУ┐ЎСИђтЦЌтиетцДТћ╣тЈўУДётѕЎуџёСИюУЦ┐№╝їТўЊтѕ░С╝џТў»тцДт╣│тЈ░сђѓ
тѕ░ 2016 т╣┤тЏЏтГБт║дтњї 2017 т╣┤СИђтГБт║д№╝їТЃЁтєхТЏ┤СИЦжЄЇсђѓТѕЉС╗гТюЅСИђС║ЏтЦйжА╣уЏ«№╝їтцДт«ХжЃйуЃДжњ▒№╝їС╗ќС╗гТ▓Ажњ▒уЃД№╝їТюђтљјТюЅСИђжЃетѕєуєгСИЇСйЈт░▒тъ«ТјЅ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жѓБСИфжўХТ«хУ░ЂТў»ТЅЊуа┤УДётѕЎсђЂСИЇТїЅуЁДС╝ау╗Ъ VC уџёујЕТ│ЋТЮЦујЕуџё№╝Ъ
тѕўУі╣№╝џТ╗┤Т╗┤уџёТіЋУхёС║║ујІтѕџ№╝їУЎйуёХС╗ќСИЇТў»Тю║ТъёТіЋУхёС║║№╝їСйєС╗ќућеСИђуДЇС║ДСИџУхёТюгтФЂТјЦтюетѕЏСИџтЁгтЈИСИіС╗јУђїТћ╣тЈўУАїСИџуџёТЅЊТ│Ћ№╝їтЄГСИђти▒С╣ІтіЏ№╝їТііУ┐ЎСИфт▒ђтЂџтЙЌУ┐ЎС╣ѕтцДсђѓТѕЉУДЅтЙЌујІтѕџтюеУ┐ЎжЄїТў»СИђСИфуюЪТГБуџё Game Changerсђѓ┬а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тЪ║жЄЉС╣ЪтЄ║уј░тѕєтїќ№╝їСИђуДЇтЂџ mega fund№╝ѕУХЁтцДтъІтЪ║жЄЉ№╝Ѕ№╝їућеУдєуЏќуџёТќ╣т╝ЈТЮЦтЂџТіЋУхё№╝ЏтЈдСИђуДЇТЁбУђїУЂџуёд№╝їУ┐йТ▒ѓСИђтЄ╗тЇ│СИГсђѓСйЋТЌХт░ЉТіЋу▓ЙтЂџТюЅТЋѕ№╝їСйЋТЌХУдєуЏќТђДТЅЊТ│ЋТЏ┤ТюЅТЋѕ№╝Ъ
тѕўУі╣№╝џТіЋУхёУАїСИџуџётЏъТіЦтЈ»С╗ЦтѕєСИцуДЇ№╝џ╬▓ тЏъТіЦтњї ╬▒ тЏъТіЦсђѓ╬▓ Тў»у│╗у╗ЪТђДТћХуЏі№╝ї╬▒ Тў»уюЪТГБуџёТіЋУхёУХЁжбЮТћХуЏісђѓУдєуЏќтъІТЅЊТ│ЋуџётЏъТіЦТЏ┤ТјЦУ┐Љ ╬▓сђѓСйєтЈфТюЅСйажђЅтЙЌтЄє№╝їСйаТЅЇУЃйтѕЏжђаТЏ┤тЦйуџё ╬▒ тЏъТіЦсђѓ
mega fund уџёТїЉТѕўтЈ»УЃйТЅЇтѕџтѕџт╝ђтДІРђћРђћтЏъТіЦС╝џжЮбСИ┤тЙѕтцДтјІтіЏсђѓ┬а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ТёЈУ»єтѕ░УхёжЄЉУДёТеАТў»СИђСИфтиетцДуџётЈўжЄЈтљј№╝їС║ћТ║љтЂџС║єС╗ђС╣ѕ№╝Ъ
тѕўУі╣№╝џуггСИђТѕЉС╗гт╝ђтДІТіЋТіђТю»сђЂС╝ЂСИџт║ћуће№╝їуггС║їТў»ТіітЪ║жЄЉУДёТеАтЂџтцДсђѓ┬а
С║ћтЁГт╣┤тЅЇТѕЉС╗гт╝ђС║єСИђСИфТѕўуЋЦС╝џ№╝їС╗ЦтЅЇтЈфУЂџуёдтюеТХѕУ┤╣С║њУЂћуйЉ№╝їС╝џтљјТѕЉС╗гтє│т«џтЁ│Т│ет║Ћт▒ѓТіђТю»тњїС╝ЂСИџТюЇтіАсђѓС╗ітцЕТѕЉС╗гТЅђТюЅтњї AIсђЂтцДТЋ░ТЇ«сђЂС║ЉУ«Ау«ЌсђЂС║ДСИџС║њУЂћуйЉТюЅтЁ│уџёжА╣уЏ«УХЁУ┐Є 50 т«ХсђѓТѕўуЋЦС╝џтљјТѕЉС╗гт░▒ТіЋУхёС║єтЋєТ▒цсђЂтю░т╣│у║┐уГЅсђѓ
ТѕЉС╗гС╗ітцЕуџёТЅЊТ│ЋТў»тЇЄу║Дуџё ╬▒ ТЅЊТ│Ћ№╝їтюетцџС║ДСИџтњїтцџжўХТ«хт»╗ТЅЙ╬▒тЏъТіЦуџётЈ»УЃйсђѓтљїТЌХ№╝їС╣ЪУдЂУ┐ЏСИђТГЦУ┐Џтїќ№╝їтГдС╣аУдєуЏќтъІТЅЊТ│ЋуџёС╝ўуѓ╣сђѓт╣┐т║дСИі№╝їтЂџТЏ┤тЦйуџёжА╣уЏ«УдєуЏќ№╝їСйєСИЇСИђт«џТіЋ№╝ЏТи▒т║дСИі№╝їТіЋУхёТаЄтЄєСИЇУЃйжЎЇСйј№╝їСйєт║ћУ»ЦТюЅТЏ┤тцџуџёУААжЄЈу║гт║дсђѓТѕЉС╗гуггС║ћТюЪтЪ║жЄЉУъЇС║є 10 С║┐уЙјтЁЃ№╝їС╗ЦтЅЇТѕЉС╗гтЈфуюІТЌЕТюЪ№╝їуј░тюеТѕЉС╗гтЈ»С╗ЦуюІСИГтљјТюЪ№╝їтюеСИђСИфУхЏжЂЊжЄїТііТЏ┤тцџуџётЁгтЈИуюІтЙЌТЏ┤ТИЁТЦџ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ТюЅСИцуДЇтЪ║жЄЉ№╝їСИђуДЇТў»тЏ┤у╗ЋСИђСИфС║║№╝їТЅђТюЅС║║Тў»С╗ќУЃйтіЏуџёт╗ХС╝И№╝ЏтЈдСИђуДЇТў»ТюЅтљѕС╝ЎС║║№╝їжђџУ┐Єт╗║уФІСИђСИфТЏ┤у┤Дт»єуџётЁгтЈИСйЊу│╗ТЮЦУ┐љУйг№╝їС║ћТ║љТЏ┤тЂЈтљЉС║јтЊфСИђуДЇ№╝Ъ┬а
┬атѕўУі╣№╝џТѕЉС╗гТў» hybrid№╝ѕТиитљѕуЅЕ№╝ЅсђѓТ»ЈСИфтЪ║жЄЉжЃйУдЂТюЅУЄфти▒уџёТаИт┐Ѓ№╝їСйєСИЇт║ћУ»ЦУ«ЕтЁХС╗ќС║║тЈфТў»тЈўТѕљТЅІтњїУёџ№╝їт«Ѓт║ћУ»ЦтЁитцЄУ«ЕТ»ЈСИфС║║жЃйТюЅтЈ»УЃйТѕљСИ║ТаИт┐ЃуџёТйютіЏтњїТю║С╝џсђѓ
┬аТѕЉТЃ│т╗║уФІСИђСИфС╗ЦТѕЉСИ║ТаИт┐ЃсђЂУЃйтцЪУхІУЃйуџёу╗ёу╗Є№╝їУ«ЕТ»ЈСИфС║║жЃйтЙЌтѕ░т┐ФжђЪТѕљжЋ┐сђѓТјЦСИІТЮЦТБђжфїТѕЉуџёСИЇТў»УЃйТїБтцџт░Љжњ▒№╝їУђїТў»УІЦт╣▓т╣┤С╣Ітљј№╝їТѕЉжђђС╝ЉС║є№╝їС║ћТ║љСЙЮуёХТў»СИђу║┐тЊЂуЅїсђѓ
┬а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тдѓСйЋС╝аТЅ┐Тќ╣Т│ЋУ«║УЃїтљјуџёТќ╣Т│ЋУ«║№╝Ъ
┬атѕўУі╣№╝џСИђСИфт╣┤Уй╗С║║тіатЁЦтѕФуџётЪ║жЄЉ№╝їСИђт╣┤УЃйТіЋ 6 СИфжА╣уЏ«№╝їтюеТѕЉС╗гУ┐ЎжЄїСИђт╣┤УЃйТіЋСИђСИцСИфт░▒тЙѕтЦйС║є№╝їУђїСИћУдЂтЂџтцДжЄЈтиЦСйю№╝їУ┐ЎТў»ТѕЉС╗гуџёСйЊу│╗тюеУхиСйюуће№╝їт«ЃУдЂТ▒ѓСйаТюЅУ«цуЪЦсђѓ
┬аС║ћТ║љуюЪТГБуџёТѕљтіЪТў»УЃйСИЇУЃйтЈўТѕљСИђСИфуЪЦУ»єу╗ёу╗Є№╝їтїЁТІгт╗║уФІуЪЦУ»єуџётЪ║уАђУ«ЙТќйтњїтиЦСйюТќ╣Т│ЋсђЂТхЂуеІтњїТ▓ЪжђџТќ╣т╝Ј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тдѓСйЋуљєУДБтЉеТюЪ№╝ЪС╗јтЉеТюЪСИГтГдС╣атѕ░С╗ђС╣ѕ№╝Ъ
тѕўУі╣№╝џТѕЉУ«цСИ║ТюЅСИЅСИфтЉеТюЪ№╝їу╗ЈТхјтЉеТюЪсђЂуДЉТіђтЉеТюЪтњїУхёТюгтЉеТюЪсђѓС╗ітцЕтцёС║јСИђСИфтцЇТЮѓтЉеТюЪ№╝їУхёТюгтЉеТюЪТ│АТ▓Фтїќ№╝їу╗ЈТхјтЉеТюЪтцётюетіеУЇАућџУЄ│СИІУАїжўХТ«х№╝їуДЉТіђтЉеТюЪтЈѕтюеСИђСИфТ┤╗УиЃуџётљЉСИіжўХТ«хсђѓ
СйаТЌаТ│Ћу«Ауљє№╝їС╣ЪТЌаТ│ЋжбёТхІтЉеТюЪсђѓтћ»СИђуџёТќ╣Т│Ћт░▒Тў»т░йжЄЈУі▒ТЌХжЌ┤УиЪТюђтЦйуџётЁгтЈИтюеСИђУхи№╝їС╗ЦтЈіСИЇУдЂжЎЇСйјТіЋУхёТаЄтЄє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тцЇТЮѓтЉеТюЪТЌХ№╝їУдєуЏќТђДТЅЊТ│ЋТў»тљдСИЇтєЇжѓБС╣ѕТюЅТЋѕ№╝Ъ
┬атѕўУі╣№╝џУдєуЏќТђДТЅЊТ│Ћт░▒Тў»СИђуДЇТќ╣Т│Ћ№╝їУ┐ЎуДЇТќ╣Т│ЋТюЅт«ЃТюЅТЋѕуџёСИђжЮб№╝їТѕЉуЏИС┐АТЅђТюЅтЂџУдєуЏќТђДТЅЊТ│ЋуџёС║║жЃйС╝џт╝║У░ЃУдЂУдєуЏќтЙЌтЄєСИђуѓ╣сђѓ
РђюТѕЉуќ»уІѓуџёС┐Ат┐ЃтЈЌТЇЪРђЮ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С║ћТ║љуюІСИітј╗у│╗у╗ЪТђДжћЎУ┐ЄС║єТЋ┤СИфућхтЋєУхЏжЂЊсђѓ
тѕўУі╣№╝џТѕЉС╗гт»╣ућеТѕитъІсђЂС║ДтЊЂтъІсђЂтиЦтЁитъІсђЂТхЂжЄЈтъІуџётЁгтЈИ№╝їТіЋтЙЌжЃйУ┐ўСИЇжћЎсђѓСйєСИђтѕ░С║цТўЊтъІтЁгтЈИ№╝їТѕЉС╗гТіЋтЙЌСИЇтЦйсђѓ
ТЌЕТюЪтњїТѕЉС╗гУхёжЄЉу╗ЊТъёТюЅтЁ│у│╗№╝їТюђтѕЮтюет«ХТЌЈтЪ║жЄЉ№╝їТѕЉС╗гТюгУЃйС╝џтј╗т»╗ТЅЙуА«т«џТђДжФўуџёжА╣уЏ«сђѓтйЊТЌХтєЁжЃеТюЅСИђСИфтјЪтДІтЄєтѕЎРђћРђћРђюУ┐ЎТў»Сйауџёжњ▒СйаТіЋтљЌ№╝ЪРђЮ ућхтЋєУ┐ЎуДЇУхёТюгт»єжЏєтъІуџёТіЋУхё№╝їТѕЉС╗гтюеуГќуЋЦСИіжЂ┐тЁЇсђѓ
тљјТЮЦТў»ТѕЉС╗гт»╣У┐ЎСИфжбєтЪЪуџёУ«цуЪЦСИЇтдѓтѕФС║║сђѓТѕЉС╗гТЏЙу╗ЈТюЅТю║С╝џТіЋу╗ЎС║гСИю 1000 СИЄуЙјтЁЃ№╝їТ▓АТіЋТў»тЏаСИ║ТѕЉС╗гтѕцТќГУ┐Ўт«ХтЁгтЈИтЈ»УЃйУдЂУъЇтЄаС║┐уЙјжЄЉ№╝їТіЋуггСИђугћ 1000 СИЄСИЇжџЙ№╝їСйєТѕЉС╗гтЮџТїЂжЋ┐ТюЪТїЂу╗ГТіЋУхё№╝їтљјжЮбС║гСИюТЮЦТЅЙТѕЉУъЇжњ▒№╝їу╗ЎСИЇу╗Ў№╝ЪТюгУ┤еУ┐ўТў»т»╣ућхтЋєуџёУ«цуЪЦСИЇтцЪ№╝їТЅЇСИЇТЋбтЂџуќ»уІѓуџёС║І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СИ║С╗ђС╣ѕСИЇтЁѕТіЋУ┐Џтј╗ 1000 СИЄуЙјтЁЃ№╝їСИІСИђУй«ТіЋСИЇТіЋтєЇУ»┤сђѓ
тѕўУі╣№╝џУ┐ЎТў»СИђСИфжЮътИИтЮЈуџёТіЋУхёт┐ЃТђЂсђѓСйатЈфУдЂтюеСИђСИфжА╣уЏ«СИіТіЋТю║№╝їСйатюеТ»ЈСИфжА╣уЏ«жЃйС╝џТіЋТю║№╝їтє│уГќт░▒С╣▒С║єсђѓ┬а
тдѓТъюСйаТ▓АТюЅтЂџтЦйТїЂу╗ГСИІТ│еуџётЄєтцЄ№╝їУ»┤ТўјСйаСИЇТў»тЮџт«џтю░уюІтЦй№╝їжѓБСйаУ┐ъУ┐Ў 1000 СИЄжЃйСИЇт║ћУ»ЦТіЋ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СйаС╗гС╣ЪТў»ТюђТЌЕуюІУ┐ЄТІ╝тцџтцџСйєТ▓АТіЋуџётЪ║жЄЉС╣ІСИђсђѓ
тѕўУі╣№╝џУ┐ЎТў»ТѕЉТї║тцДуџёСИђСИфжЂЌТєЙсђѓтйЊТЌХТѕЉТћ»ТїЂТіЋ№╝їС║ћТ║љТЅђТюЅС║║жЃйтЈЇт»╣№╝їТѕЉт▒ѕТюЇС║єсђѓтЏаСИ║ТѕЉС╗гтюетЈдтцќСИђСИфућхтЋєтЁгтЈИСИітѕџтѕџУЙЊТјЅС║єтЄатЇЃСИЄуЙјжЄЉсђѓУђїТІ╝тцџтцџтЈѕтѕџтЦйтюеС╗јТІ╝тЦйУ┤Д№╝ѕУЄфУљЦ№╝ЅтљЉТІ╝тцџтцџ№╝ѕт╣│тЈ░№╝ЅУйгтъІуџёУ┐ЄуеІСИГ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СйаТюЅСИфУДѓуѓ╣Тў»ТіЋУхёУдЂТіЋж╗ЉтцЕж╣Ё№╝їТЅђТюЅС║║жЃйСИЇтљїТёЈуџёТЌХтђЎ№╝їтЈЇУђїт║ћУ»ЦТіЋсђѓ┬а
┬атѕўУі╣№╝џТѕЉС╗гУ┐ўТў»СйјС╝░С║єСИцС╗ХС║І№╝їСИђТў»тЙ«С┐АуџёТхЂжЄЈу║бтѕЕТЅђтИдТЮЦуџёу│╗у╗ЪТђДТю║С╝џ№╝ЏС║їТў»ТѕЉСйјС╝░С║єж╗ёт│ЦУЃйтцЪТіітЙ«С┐АТхЂжЄЈуДЂтЪЪУ┐љУљЦуџёУЃйтіЏсђѓ
тљјТЮЦТѕЉС╗гтЈЇТђЮ№╝їТѕЉС╗гт»╣ТЋ┤СИфућхтЋєу│╗у╗ЪТђДжћЎУ┐Є№╝їТЌЕТюЪТў»тЏаСИ║тЪ║жЄЉу╗ЊТъё№╝їтљјжЮбТў»тЏаСИ║У«цуЪЦСИіСИЇт╝║сђѓтєЇтљјжЮбТѕЉС╗гТёЈУ»єтѕ░ТЋ┤СИфС║цТўЊтъІУАїСИџТў»СИфтиетцДТю║С╝џуџёТЌХтђЎ№╝їС╗ЦС║ћТ║љуџёУхёжЄЉСйЊжЄЈУдЂТіЋућхтЋєтЁгтЈИ№╝їТіЋСИЇтіе№╝їТЅђС╗ЦТѕЉС╗гТЅЇтє│т┐ЃТЅЕтцДУДёТеА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ТЅђС╗ЦтйЊТЌХСйат▒ѕТюЇС║є№╝їУ┐ўТў»тЏаСИ║СИЇтцЪуќ»уІѓсђѓ
тѕўУі╣№╝џТѕЉуќ»уІѓуџёС┐Ат┐ЃтЈЌТЇЪсђѓ
┬а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тцДуџётЋєСИџТю║С╝џТў»жЮътИИт░Љуџё№╝їУ┐Єтј╗тЇЂт╣┤тЁеСИќуЋїУ»ъућЪуџёТЅђТюЅТќ░тЁгтЈИжЄї№╝їТюђтђ╝жњ▒уџётцДТдѓујЄТў»тГЌУіѓтњїуЙјтЏбСИцт«ХсђѓС║ћТ║љТіЋСИГС║єт░Ју▒│сђЂт┐ФТЅІ№╝їСйє BATсђЂTMD тіаТІ╝тцџтцџжЃйТ▓АТюЅТіЋСИГ№╝їСИ║С╗ђС╣ѕ№╝Ъ┬а
тѕўУі╣№╝џТѕЉуггСИђТгАУДЂујІтЁ┤Тў»тюежЦГтљдТЌХТюЪ№╝їС╗ќтЪ║ТюгСИЇТђјС╣ѕУ»┤У»Ю№╝їжѓБтЈ»УЃйТў»С╗ќуіХТђЂТюђти«уџёТЌХтђЎ№╝їтљјТЮЦТѕЉС╗гтЈѕу│╗у╗ЪТђД pass С║єтЏбУ┤Гсђѓж╗ёт│ЦТЏ┤тЃЈСИђСИфтњеУ»бтЁгтЈИуџёС║║№╝їТѕЉт»╣У«▓тЙЌуЅ╣тѕФТИЁТЎ░сђЂу╗ЊТъётїќуџёСИюУЦ┐ТюЅтЙѕтцДуџёУГдУДЅсђѓ┬а
тЈдтцќТѕЉС╗гтюеТЪљС║ЏжА╣уЏ«СИіТїЂС╗ЊуЏИт»╣УЙЃжЄЇ№╝їТѕЉС╗гтЁѕТіЋУхёС║єт┐ФТЅІ№╝їтГЌУіѓтјЪТЮЦтњїт┐ФТЅІТ▓АТюЅуФъС║Ѕ№╝їтљјТЮЦтЄ║уј░С║єТіќжЪ│№╝їтЈЇУ┐ЄТЮЦТѕљСИ║С║єТѕЉС╗гТіЋУхёуџёжџюубЇсђѓ┬а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тюетГЌУіѓтЈфТюЅтц┤ТЮАуџёТЌХтђЎ№╝їСйаС╗гС╣ЪТ▓АТюЅТіЋсђѓУђї 2016 т╣┤СйаС╗гУ┐ўУ»иС║єт╝аСИђжИБтЈѓтіаС║ћТ║љуџё CEO т╣┤С╝џсђѓ
┬атѕўУі╣№╝џТЂ░ТЂ░тЏаСИ║ТѕЉтЂџУ┐ЄтфњСйЊ№╝їТѕЉТи▒уЪЦтєЁт«╣С║ДСИџуЏЉу«АТў»жЮътИИтцДуџёТїЉТѕў№╝їтГЌУіѓТЌЕТюЪтцДжЄЈтЄ║уј░У┐ЄУиЪС╝ау╗ЪтфњСйЊС╣ІжЌ┤уџётє▓уфЂ№╝їТѕЉС╗гУ»ёС╝░У┐Є№╝їТііт«Ѓ pass С║єсђѓ┬а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СйаУ»┤У┐ЄСйауџёСИ╗УдЂуГќуЋЦТў»уюІС║║№╝їУДЂтѕ░т╝аСИђжИБТЌХ№╝їСйаСИЇуЏИС┐АС╗ќУЃйТѕўУЃюУ┐ЎСИђтѕЄ№╝Ъ┬а
┬атѕўУі╣№╝џтдѓТъюСйаТюЅУ┐ЄтЂџтфњСйЊуџёу╗Јжфї№╝їСйаС╝џУДЅтЙЌт«ътюеТ▓АтіъТ│ЋТљъсђѓ
т╝аСИђжИБУЃйтЂџТѕљ№╝їтЈЇУАгтЄ║ТЮЦС╗ќТў»СИђТхЂуџёС╝ЂСИџт«ХсђЂТЋбС║јтєњжЎЕ№╝їС╗ќС╗гтюеУ┐ЎСИфС║ІТЃЁСИітЈ»УЃйжЃйУиеУХіС║єС╗ЦтЅЇтЙѕтцџС║║ТІЁт┐ЃуџёУ┐ЎСИфС║І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жћЎУ┐ЄС╗ЦСИіжА╣уЏ«№╝їТў»тљдтњїСйаСИфС║║уџёТђДТа╝сђЂУДєУДњТюЅтЁ│№╝Ъ
тѕўУі╣№╝џтцфУЄфТ┤йсђЂтцфу╗ЊТъётїќуџёСИюУЦ┐ТѕЉС╝џуЅ╣тѕФУГдТЃЋ№╝їтЏаСИ║тѕЏСИџтњїТіЋУхёжЃйТў»жЄЈтГљТђЂсђѓ┬а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СйаС╝џт«╣ТўЊт┐йУДєС╗ђС╣ѕ№╝Ъ┬а
тѕўУі╣№╝џТѕЉС╣аТЃ»ућеСИђСИфжЋ┐ТюЪтЈ»ТїЂу╗ГТђДуџёТќ╣т╝ЈТЮЦУ┐ЄТ╗цтЁгтЈИсђѓТЅђС╗ЦТѕЉт»╣т┐ФжђЪтЈўтїќуџёСИюУЦ┐№╝їС╝џт«╣ТўЊТііт«ЃУ┐ЄТ╗цТјЅ№╝їтЏаСИ║СИЇТў»ТЅђТюЅт┐ФжђЪтЈўтїќуџёСИюУЦ┐жЃйтЁиТюЅжЋ┐ТюЪтЈ»ТїЂу╗ГТђД№╝ї
Т»ћтдѓж╗ёт│ЦУиЪТѕЉУ«▓№╝їтЙ«С┐АуџёТхЂжЄЈу║бтѕЕТў»СИђСИфтиетцДуџёУїЃт╝ЈтЈўтїќ№╝їСИђСИфтиетцДуџёТю║С╝џ№╝їСйєТѕЉС╝џУ«цСИ║№╝їтЙ«С┐АТхЂжЄЈу║бтѕЕСИЇТў»С╗ќуџёсђѓ
С║Іт«ъУ»ЂТўјТѕЉСйјС╝░С║єж╗ёт┤бТіітЙ«С┐АТхЂжЄЈуДЂтЪЪтїќуџёУЃйтіЏ№╝їС╗ЦтЈіТѕЉСйјС╝░С║єтЙ«С┐Ауџёт«╣т┐Їт║д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Тў»тљдТюЅТЪљС║ЏтЁ▒тљїтЏау┤ат»╝УЄ┤СйажћЎУ┐ЄС║єтц┤ТЮАтњїТІ╝тцџтцџ№╝ЪТ»ћтдѓСйат»╣УДётѕЎуџётюеТёЈ№╝їС╗ЦтЈіт»╣С║јУ┐ЎС║ЏС╝ЂСИџт«ХтЈ»С╗ЦућежЮътИИУДёТЅІТ«хТЅЊуа┤УДётѕЎ№╝їСйаТ▓АТюЅжбёТќЎтѕ░сђѓ┬а
тѕўУі╣№╝џУ┐ЎСИЇТў»ТѕЉС╗гуюЪТГБуџёжЌ«жбўсђѓТѕЉС╗гуюЪТГБуџёТїЉТѕўТў»№╝їС║ћТ║љтюеС╝ЂСИџСИГтљјТ«хТЌХТюЪуџёТіЋУхёСИіТ▓АТюЅС╝ўті┐сђѓТѕЉС╗гућетЄ╗СИГС╝ЂСИџуџёТќ╣т╝ЈТЮЦтЂџТіЋУхё№╝їт«ЃСИђт«џТЁбСИћУЂџуёдсђѓТ▓ѕтЇЌж╣ЈтЂџТіЋУАїтЄ║У║Ф№╝їу║бТЮЅт»╣УдєуЏќТЅЊТ│ЋТў»тЙѕтЮџтє│уџё№╝їТЅђС╗ЦуггСИђтцЕТѕЉС╗гСИцСИфТіЋУхёТќ╣Т│Ћт░▒тѕєтїќсђѓ
С╗ітцЕТђјС╣ѕтюетЪ║жЄЉуџёУДёТеАсђЂТіЋУхёТќ╣Т│ЋС╗ЦтЈіу│╗у╗ЪТђДТЇЋТЇЅтѕ░тЦйтЁгтЈИ№╝їТ»ЈСИфС║║жЃйтюежЮбСИ┤уЮђСИЇтЈ»УЃйСИЅУДњтйбсђѓТѕЉС╗гС╣ЪтюеуЏИС║њтГдС╣асђѓу║бТЮЅС╗іт╣┤ТјетЄ║С║є 3 С║┐уЙјтЁЃСИЊжЌеТіЋТЌЕТюЪуџётЪ║жЄЉ№╝їУђїТѕЉС╗гС╗јТЌЕТюЪтИїТюЏтљЉСИГтљјуФ»УћЊт╗Хсђѓ
У┐ЄС║јУ┐йТ▒ѓу╗ѕт▒ђуџёТЌХтђЎ№╝їТѕЉС╗гти▓у╗ЈтюеТЌХтѕ╗ТЈљжєњУЄфти▒№╝їт»╣тЈўтїќУдЂуЅ╣тѕФТЋЈТёЪ№╝їСйєТѕЉС╗гтЈѕСИЇТў»жѓБуДЇтѕФС║║ТЅђУ░ЊуџёТЋЈТёЪРђћРђћтЈфУдЂТюЅТїЄТаЄСИітЇЄт░▒ТіЋУхёРђћРђћТѕЉС╗гУ┐ўУдЂУ┐йжЌ«№╝їт«ЃуџёжЋ┐ТюЪтЈ»УАїТђД№╝їУ┐Ўт┐ЁуёХС╝џтИдТЮЦтѕџТЅЇУ»┤уџё miss№╝ї miss т░▒Тў»ТѕЉС╗гуџёТЅЊТ│Ћсђѓ┬а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Сйати▓у╗Ју«АС║єУХЁУ┐Є 30 С║┐уЙјтЁЃсђѓТїЅуЁДС║ћТ║љуј░тюеуџёТЅЊТ│Ћ№╝їСйаУ«цСИ║УЄфти▒ТюђтцџтЈ»С╗Цу«Атцџт░Љжњ▒№╝Ъ
тѕўУі╣№╝џу«А 100 С║┐уЙјжЄЉТ▓АС╗ђС╣ѕжЌ«жбў№╝їућџУЄ│ТЏ┤тцД№╝їСйєт«ЃжюђУдЂСИђТГЦСИђТГЦсђѓ
РђюVC т»╣У┐ЎСИфСИќуЋїТюђжЄЇУдЂуџёТёЈС╣ЅТў»тѕЏжђаТхЂтіеТђДсђѓРђЮ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Сйа 1999 т╣┤тЁЦУАї№╝їУ┐ўТюЅТ»ћСйаС╗јСИџТЌХжЌ┤ТЏ┤жЋ┐№╝їСЙЮуёХТ┤╗УиЃтюеСИђу║┐уџёСИГтЏйТіЋУхёС║║тљЌ№╝Ъ
тѕўУі╣№╝џт║ћУ»ЦТюЅтљД№╝їтЃЈуЂФт▒▒уЪ│УхёТюгуџёуФаУІЈжў│сђѓТѕЉтЁЦУАїТЌХТЅЇ 26 т▓Ђ№╝їТГцтљјСИђуЏ┤тюеУ┐ЎСИфУАїСИџ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СйатЂџТіЋУхёТ▓АТюЅтИѕТЅ┐№╝їжЃйжЮаУЄфти▒ТЉИу┤бсђѓт»╣СйаТЮЦУ»┤ТюђТюЅТЋѕуџётГдС╣аТќ╣Т│ЋТў»С╗ђС╣ѕ№╝Ъ┬а
тѕўУі╣№╝џТЅђТюЅС║║жЃйТў»ТѕЉуџёУђЂтИѕсђѓтљїС║ІТюЅТЌХтђЎСИЇуљєУДБ№╝їТѕЉТўјТўЙСИЇС╝џТіЋУ┐ЎСИфС║║№╝їСИ║С╗ђС╣ѕУ┐ўУдЂУі▒СИцСИЅСИфт░ЈТЌХтњїт»╣Тќ╣УЂісђѓтЁХт«ъТѕЉтюетГдС╣а№╝їтЊфТђЋСИЇТіЋ№╝їТѕЉУ┐ўТў»ТЃ│жђџУ┐ЄС╗ќС║єУДБУ┐ЎУАїСИџжЄїТюЅС║║тюетЂџС╗ђС╣ѕТюЅУХБуџёС║ІсђѓтЈдтцќт░▒Тў»С║║т«ХТЮЦСИђУХЪТї║СИЇт«╣ТўЊсђѓ
ТѕЉуџёжўЁУ»╗тњїтЁ┤УХБС╣Ът║ъТЮѓт╣┐Т│Џ№╝їТѕЉС╝џуюІт«ЌТЋЎсђЂтјєтЈ▓сђЂС║║ТќЄсђЂуцЙС╝џтѕХт║дтЈўУ┐ЂуГЅСИюУЦ┐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тњїТ»ЈСИфтѕЏСИџУђЁжЃйУЂіСИцСИфт░ЈТЌХ№╝їтЊфТюЅТЌХжЌ┤уюІУ┐ЎС╣ѕтцџСИюУЦ┐№╝Ъ┬а
тѕўУі╣№╝џТѕЉтцёуљєС┐АТЂ»уџёу╗ЊТъётїќУЃйтіЏтЙѕт╝║№╝їтцёуљєжђЪт║дтЙѕт┐ФсђѓСИђС║ЏтЙѕтцЇТЮѓТѕќТў»жџЈТю║сђЂуљљубјуџёС║ІТЃЁ№╝їТѕЉуџёУёЉтГљС╝џтѕєжЌетѕФу▒╗Тііт«ЃУ┐ЁжђЪтЈўТѕљТѕЉуџёУ«цуЪЦ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тдѓСйЋУ┐ЁжђЪтѕцТќГСИђСИфС║║№╝Ъ
тѕўУі╣№╝џждќтЁѕСйаУдЂт»╣С║ІТЃЁСИІтіЪтцФсђѓтйЊТѕЉтюеСИђСИфС║ІСИіуџёУ«цуЪЦУЙЙтѕ░СИђт«џТ░┤тЄє№╝їтдѓТъютѕЏСИџУђЁтюеУ«цуЪЦСИіУХЁтЄ║ТѕЉ№╝їжђџтИИС╗ќти▓у╗ЈтЙѕуеђу╝║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С╗јС║ІТіЋУхёУ┐ЎС╣ѕтцџт╣┤№╝їУѓ»т«џУДЂУ┐ЄтЙѕтцџТ«ІжЁитњїУЇњУ░гС╣ІС║ІсђѓтЈ»тљдтѕєС║ФСИђСИфСйаТЅђУДЂуџёТюђТ«ІжЁиС╣ІС║І№╝Ъ
тѕўУі╣№╝џТѕЉтѕџтЁЦУАїТ▓АтцџС╣Ё№╝їСИђСИфТіЋУхёжА╣уЏ«тѕЏтДІС║║ућЪуЌЁтј╗СИќсђѓС╗ЦтЈіСИђС║ЏтЁгтЈИТюђтљјтЁ│жЌе№╝їУ┐ЎС║ЏУ┐ЄуеІжЃйТї║Т«ІжЁиуџё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С╝џТіЋУхёУ┐ъу╗Гтц▒У┤ЦуџётѕЏСИџУђЁтљЌ№╝Ъ
тѕўУі╣№╝џТѕЉС╗гТё┐ТёЈУ┐ъТіЋСИЅТіісђѓтц▒У┤ЦСИђТгАтєЇТіЋСИђТгА№╝їтєЇтц▒У┤ЦтєЇТіЋСИђТгА№╝їтйЊуёХСИЇТў»С╗ђС╣ѕС║║тц▒У┤ЦжЃйТіЋсђѓт»╣С║јуюЪТГБС╝ўуДђуџёС║║№╝їтц▒У┤ЦТў»С╗ќТюђтцДуџёУ┤бт»ї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СИЅТгАТў»СИђСИфуЋїжЎљсђѓ
тѕўУі╣№╝џСИЅТгАТў»СИђСИфС║║Тюђж╗ёжЄЉуџётѕЏСИџТЌХжЌ┤тњїУ»ЋжћЎУЃйтіЏсђѓСИЅТгАтєЇСИЇТѕљтіЪ№╝їтЏът«ХТЪЦТЪЦуЦќтЮЪ№╝їТЪЦТЪЦт«ХУ░▒№╝їУ┐љТ░ћтцфти«С║є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СйаУ»┤У┐ЎтЈЦУ»ЮуџёТЌХтђЎт░▒Тї║Т«ІжЁиуџёсђѓ
тѕўУі╣№╝џУ┐ЎСИфУАїСИџТў»СИђСИфтІЄТЋбУђЁуџёТИИТѕЈ№╝їТѕЉС╗гУЃйтЂџтЙЌТюЅТИЕт║д№╝їСИЇС╗БУАеуЏ▓уЏ«т┐ЃУй»сђѓугдтљѕТѕЉС╗гуџёТаЄтЄєсђЂУЃйТюЅУхёТа╝тц▒У┤ЦуџёС║║№╝їСИђТгАтц▒У┤ЦС╝џУ«ЕС╗ќСИІСИђТгАТѕљтіЪТдѓујЄТЈљжФў 30% С╗ЦСИі№╝їСИцТгАтц▒У┤Цт░▒ТюЅТю║С╝џТЈљжФў 60%сђЂ70%№╝їСИЅТгАтєЇСИЇТѕљтіЪ№╝їтЈ»УЃйтГўтюеСИђС║Џу│╗у╗ЪТђДжЌ«жбўТў»жЋ┐ТюЪуфЂуа┤СИЇС║єуџё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СйатИїТюЏтѕЏСИџУђЁтдѓСйЋуюІтЙЁСйа№╝Ъ
тѕўУі╣№╝џТѕЉтИїТюЏТѕљСИ║тѕЏСИџУђЁТюђТюЅтй▒тЊЇтіЏуџёС║║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тюе cap table СИі№╝Ъ
тѕўУі╣№╝џтюетЁ│у│╗тњїС┐АС╗╗т║дСИісђѓтѕЏСИџУђЁжЮътИИтГцуІг№╝їС╗ќС╗гжюђУдЂТЏ┤тцџС║║ТЮЦтИ«С╗ќС╗гт╝ђТІЊУДєжЄј№╝їТѕќУђЁтюетЁ│жћ«ТЌХтѕ╗СИ║С╗ќтЂџжФўУ┤ежЄЈуџёУЂєтљг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тйЊСИђСИфтѕЏСИџУђЁУ»┤С╗ќтЙѕуЌЏУІдТЌХ№╝їСйаС╝џтдѓСйЋт«ЅТЁ░№╝Ъ
┬атѕўУі╣№╝џТЅђТюЅС╝ЂСИџт«ХжЃйжЮътИИуЌЏУІд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т«┐тЇјТў»СИђСИфтЙѕуЅ╣тѕФуџётѕЏСИџУђЁ№╝їС╗ќуџёуЌЏУІдТЮЦУЄфС╗ђС╣ѕ№╝Ъ┬а
┬атѕўУі╣№╝џт«┐тЇјТюЅТї║тјЪућЪТђЂуџёуЌЏУІдсђѓт┐ФТЅІС╗ітцЕуџёТѕљжЋ┐жђЪт║дт»╣С╗ќС╗гТЮЦУ»┤Тў»СИђСИфтиетцДТїЉТѕў№╝їтдѓСйЋжЕЙжЕГтњїу«АуљєСИђСИфжФўжђЪТѕљжЋ┐уџёС╝ЂСИџ№╝їУ┐юУХЁтЄ║С║єС╗ќС╗гС╗ЦтЅЇуџёу╗ЈжфїтњїУЃйтіЏ№╝їС╗ќуЌЏУІдтЙѕТГБтИИсђѓ┬а
СИђугЉСИіТгАУДЂжЮбт»╣ТѕЉУ»┤№╝їС╗ќС╗гт«їтЁеСйјС╝░С║єућеТѕиуџёУДёТеАтњїжюђТ▒ѓ№╝їтдѓТъюС╗ітцЕУЃйтЮљТЌХуЕ║уЕ┐ТбГТю║тЏътј╗№╝їт┐ФТЅІт║ћУ»ЦТюЅТЏ┤Т┐ђУ┐ЏуџёУъЇУхётњїС║ДтЊЂуГќуЋЦсђѓ
┬а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тј╗т╣┤жЄЄУ«┐ТЌХСйаУ»┤ТюђтЁ│т┐Ѓт┐ФТЅІуџёу╗ёу╗ЄжЌ«жбў№╝їСйєС╗ітцЕУ┐ЎСИфжЌ«жбўС╝╝С╣јТ▓АТюЅтЙЌтѕ░УДБтє│№╝їтЈЇУђїТЏ┤тцДС║єсђѓ
┬атѕўУі╣№╝џтцДт«Хт«╣ТўЊУбФС║ІС╗ХТћЙтцДсђѓСИђСИфтЁгтЈИтЈфТюЅтюетЈўжЮЕТЌХТЅЇС╝џтЄ║уј░ТЉЕТЊд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ТѕЉС╗гтљгУ»┤СИђСИфТЋЁС║І№╝їСИђтљЇтѕЏСИџУђЁУ┤фТ▒АУбФСИЙТіЦ№╝їСйєТюђтљјС╗ќСИјТіЋУхёС║║УЙЙТѕљтЇЈУ««РђћРђћТіЋУхёС║║СИЇУхиУ»Ѕ№╝їС╗ќжђђтЄ║ТЅЙСИђСйЇТќ░ CEO№╝їТіЋУхёС║║уГћт║ћС║єсђѓТЇбСйаС╝џТђјС╣ѕтЂџ№╝Ъ
тѕўУі╣№╝џТѕЉС╗гТЏЙу╗ЈТюЅтѕЏСИџУђЁтЂџС║єСИЇтЦйуџёС║І№╝їС╗ќТЈљтЄ║ТіітЁгтЈИтЇќТјЅУ«ЕТѕЉС╗гТїБжњ▒№╝їСйєТѕЉС╗гСИЇТјЦтЈЌсђѓтдѓТъюС╗ќтюеТѕЉС╗гСИЇуЪЦТЃЁТЌХТіітЁгтЈИтЇќТјЅ№╝їжѓБТѕЉС╗гУЃйТјЦтЈЌсђѓТѕЉС╗гСИЇУЃйТјЦтЈЌтњїС╗ќСИђУхижфЌтѕФС║║сђѓ
СйаСИ║У┐ЎТаиуџёС║║С╣░СИђТгАтЇЋ№╝їтљјжЮбТђјС╣ѕтіъ№╝ЪТѕЉС╗гуџёС╗итђ╝УДѓС╝џтЮЇтАїуџё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У┐ЎСИфУАїСИџСИГСйаТюђтјїТЂХС╗ђС╣ѕ№╝Ъ┬а
тѕўУі╣№╝џCheatingсђѓтЙѕтцџтЁгтЈИСИџтіАжђатЂЄ№╝їУ┐ЎТў»ТѕЉТюђСИЇтќюТгбуџё№╝їTo VC ТѕЉС╣ЪтЙѕСИЇтќюТгб№╝їTo ATMсђЂBAT ТѕЉС╣ЪСИЇтќюТгб№╝їТѕЉУ┐ўтјїТЂХтіБтИЂжЕ▒УЅ»тИЂсђѓ
ТюЅТЌХтђЎТѕЉт»╣У┐ЎС║ЏС║ІТЃЁтЁХт«ъТёЪтѕ░Тї║ suffer№╝ѕуЌЏУІд№╝Ѕуџё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СйаТЃ│уюІтѕ░СИђСИфТђјТаиуџётЋєСИџСИќуЋї№╝Ъ
┬атѕўУі╣№╝џТѕЉжѓБтцЕУиЪтГБуљд№╝ѕтЇјСйЈжЏєтЏбтѕЏтДІС║║№╝ЅУЂітцЕ№╝їТѕЉУиЪС╗ќУ»┤№╝їVC т»╣У┐ЎСИфСИќуЋїТюђжЄЇУдЂуџёТёЈС╣ЅТў»тѕЏжђаТхЂтіеТђД№╝їт░▒Тў»У«ЕСИђС║ЏТюЅТбдТЃ│ТюЅУЃйтіЏ№╝їСйєТ▓АУЃїТЎ»уџёС║║№╝їУЃйтцЪУ«ЕС╗ќС╗гТѕљтіЪсђѓТбдТЃ│уџёС╗итђ╝тњїтѕЏжђаУЃйтцЪУДБтє│тЙѕтцџжЌ«жбў№╝їТјетіеУ┐ЎСИфуцЙС╝џтЙђтЅЇУх░сђѓ
РђюТюђТѕљтіЪуџётѕЏСИџУђЁТў»жЄіУ┐дуЅЪт░╝РђЮ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СйаС╝џтдѓСйЋТЈЈУ┐░СйауџёСИќуЋїУДѓТефу║хУй┤№╝ЪтЮљТаЄУй┤уџёТћ»уѓ╣Тў»С╗ђС╣ѕ№╝Ъ┬а
┬атѕўУі╣№╝џтјєтЈ▓тњїуЅЕуљєу╗┤т║дсђѓТѕЉт»╣тјєтЈ▓тЙѕТёЪтЁ┤УХБ№╝їТѕЉУ«цСИ║тјєтЈ▓СИђуЏ┤тюежЄЇтцЇ№╝їС╗јТЮЦТ▓АТюЅтЈў№╝їтЈўуџётЈфТў»Т╝ћу╗јуџёУййСйЊ№╝їТЅђС╗ЦТѕЉт»╣СИЇтЈўуџёжђ╗УЙЉуЅ╣тѕФтЦйтЦЄсђѓ
тјєтЈ▓тЁеТў»т«ЈУДѓ№╝їУђїСИћТюЅТъЂжЋ┐ТЌХжЌ┤у╗┤т║д№╝їтЈфТў»ТѕЉС╗гуџёућЪтЉйтњїую╝уЋїУ┐ЄС║јуІГуфё№╝їТЅЇС╝џТііуЪГТЌХжЌ┤уюІтѕ░уџёСИюУЦ┐тйЊТѕљтјєтЈ▓уџётцДжђ╗УЙЉ№╝їУ«цСИ║т«ЃСИЇтЈ»уЪЦСИЇтЈ»ТхІсђѓСйєтдѓТъюСйауюІтЙЌтцЪУ┐ю№╝їТіітјєтЈ▓жђ╗УЙЉтЈЇт║ћтюеТЋ░тГдуЅЕуљєуџёуДЉтГдуљєУ«║СИі№╝їтЁХт«ът«ЃжЃйТў»т«їуЙјуџёТЏ▓у║┐№╝їТїЅуЁДТЌбт«џТГЦжфцУх░№╝їт░▒СИђт«џУЃйтѕ░СИІСИђТГЦсђѓ
С╗ју▓њтГљТђЂсђЂжЄЈтГљТђЂтј╗уюІ№╝їТЅђТюЅС║ІуЅЕжЃйТў»жџЈТю║СИћу╗Ют»╣СИЇтЈ»ТјДуџё№╝їСйєСйаТііТЅђТюЅуџётИЃТюЌУ┐љтіеТћЙтюетиетцДуџёТаиТюгжЄЈСИі№╝їтЈѕУАеуј░тЄ║т«їуЙјтњїУДётЙІТђДсђѓ
┬атЙѕтцџТіЋУхёС║║С╝џжЎитЁЦСИЇтЈ»уЪЦ№╝їТііУЄфти▒уџёТіЋТю║тйЊТѕљТюгС║ІТѕќУђЁтйЊТѕљУ┐љТ░ћсђѓСйєС║Іт«ъСИі№╝їVC тњїтѕЏСИџУђЁСИђТаи№╝їТюђУ┐иС║║уџётю░Тќ╣Тў»ТѕЉС╗гтюетЂџжЄЈтГљТђЂ№╝їУЙЊтЄ║СИђСИфт«ЈУДѓуџёу╗ЈтЁИТђЂ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СйаТЅђуюІтѕ░уџёСИЇтЈўуџёжђ╗УЙЉТюЅС╗ђС╣ѕ№╝Ъ┬а
┬атѕўУі╣№╝џТ»ћтдѓУ»┤ућхтЋєуџё Рђютцџт┐ФтЦйуюЂРђЮсђѓС║║ТђДС╣ЪТў»№╝їС║║уџёУ┤фтЕфсђЂуѕ▒ТЂеТЃЁС╗ЄсђЂжЕгТќ»Т┤ЏжюђТ▒ѓС╗јТЮЦТ▓АТюЅтЈўУ┐Є№╝їтЈфСИЇУ┐ЄтјЪТЮЦуѕ▒ТЂеТЃЁС╗Єтюеућхтй▒жЄї№╝їС╗ітцЕтюеуЪГУДєжбЉжЄї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тЊфСйЇ CEO уџёСИќуЋїУДѓУ«ЕСйаУДЅтЙЌТюђСИЇтЈ»ТђЮУ««№╝Ъ┬а
┬атѕўУі╣№╝џТђ╗СйЊСИіжЃйТї║УЄфТ┤йуџё№╝їтюетјєтЈ▓тцДжђ╗УЙЉСИІ№╝їСИђтѕЄжЃйТї║тљѕуљєсђѓ
┬а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СйаУ┐ЎуДЇт»╣ТЌХжЌ┤уџёТїЂу╗ГуџёТИ┤ТюЏТў»С╗јСйЋУђїТЮЦ№╝Ъ
тѕўУі╣№╝џтЁХт«ъТюђТѕљтіЪуџётѕЏСИџУђЁТў»жЄіУ┐дуЅЪт░╝№╝їС╗ќуџётѕЏСИџжА╣уЏ«тГўтюеС║єтЄатЇЃт╣┤сђѓТѕЉт»╣ТЅђТюЅУЃйтцЪУХЁУХіТЌХжЌ┤уџёСИюУЦ┐ТёЪтЁ┤УХБ№╝їТѕЉС╣Ът»╣УЃйтцЪУДБжЄіУ┐ЎСИфСИќуЋїуџёСИюУЦ┐ТёЪтЁ┤УХБ№╝їТѕЉтЈфТў»ТЂ░тиДСИЇт░Јт┐ЃТјЅтѕ░С║єтЋєСИџтњї VC У┐ЎСИфУАїСИџсђѓ
┬а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У┐Єтј╗С║їтЇЂт╣┤СИГтЏйС║њУЂћуйЉ№╝їСйаУДЅтЙЌтЊфСИфуъгжЌ┤ТюђТюЅТёЈТђЮ№╝їућџУЄ│ТЃ│тј╗жЌ«СИђжЌ«жѓБСИфуъгжЌ┤тйЊС║ІС║║Тў»ТђјС╣ѕТЃ│уџё№╝Ъ┬а
┬атѕўУі╣№╝џТѕЉтЙѕтЦйтЦЄжЕгС║ЉтйЊт╣┤С╗ј B2B тѕ░ C2C уџётЁ│жћ«УйгТЇб№╝їжѓБТў»СИђСИфУЅ░жџЙуџётє│уГќсђѓСИЇУ┐ЄТѕЉтљјТЮЦТЃ│ТЃ│С╣ЪСИЇтЦЄТђф№╝їжЕгС║ЉСИЇТў»СИђСИфтиЦуеІтИѕ№╝їС╣ЪСИЇТў»СИђСИфтЋєС║║№╝їС╗ќуџёУДєжЄјтЏаТГцТЏ┤т╣┐№╝їжЕгС║ЉуџёуггСИђТђДтјЪуљєТЏ┤тіатЏътйњС║║ТђДсђѓ┬а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Тў»тљдТЃ│У┐ЄтњїтГЎТГБС╣ЅСИђТаи№╝їжђџУ┐ЄТіЋУхёТЮЦт╗║уФІУЄфти▒уџёућЪТђЂсђЂУ┐ъТјЦСИЄС║┐тИѓтђ╝уџётЁгтЈИ№╝їТѕљСИ║СИђСИфтЈ»С╗ЦтњїУХЁу║ДтцДтЁгтЈИТіЌУААуџётіЏжЄЈ№╝Ъ
тѕўУі╣№╝џтцДт«ХжЃйТў»ућЪТђЂуџёСИђжЃетѕєсђѓУЃйТѕљСИ║СИђСИфућЪТђЂжЄїуџёУіѓуѓ╣№╝їућџУЄ│СИђСИфУХЁу║ДУіѓуѓ╣№╝їУ┐ЎтйЊуёХтИїТюЏсђѓ
сђіТЎџуѓ╣сђІ№╝џС╗ЦтЅЇТ▓АТЃ│У┐Є№╝Ъ
тѕўУі╣№╝џТЅђС╗Цуј░тюет╝ђтДІТъёт╗║сђѓ
- тЇ░т║дсђЂуЙјтЏйу║иу║итЄ║ТЅІ№╝їTikTokУЃйтљдтюетЁеуљЃжЎљтѕХСИГжђєжБју┐╗уЏў№╝Ъ
- 2022т╣┤ТЌЦТюгСИ╗Тю║ТИИТѕЈтИѓтю║№╝џт░Јт╣ЁтЏъТџќ№╝їУй»С╗ХжћђжЄЈСИцТъЂтѕєтїќ
- NexonтЁгтИЃDNFт╝ђТћЙСИќуЋїТќ░Сйю№╝їСйєТЅІТИИтЏйТюЇжЂЦжЂЦТЌаТюЪ№╝Ъ
- ShopeeТѕќт░єС║ј1Тюѕ13ТЌЦУхижђђтЄ║Т│бтЁ░тИѓтю║
- 2022т╣┤тЁеуљЃТЅІТИИТћХтЁЦжЎЇС║є
- Уѓ▓убДС╣ЪУдЂжЎЇТюгтбъТЋѕ№╝џуаЇ3ТгЙТИИТѕЈ№╝їТюфТЮЦ2т╣┤жЎЇТѕљТюгУХЁ2С║┐ТгДтЁЃ
- т╝ЋУхиУ░иТГїтњїУІ▒С╝ЪУЙЙТІЁт┐Д№╝їтЙ«Уй»690С║┐уЙјтЁЃТћХУ┤ГтєЇућЪТ│бТіў
- жЕгТќ»тЁІу╗Ду╗ГтјІу╝ЕTwitterТѕљТюг№╝џтЁ│жЌГтцДжЄЈТхитцќтѕєтЁгтЈИ